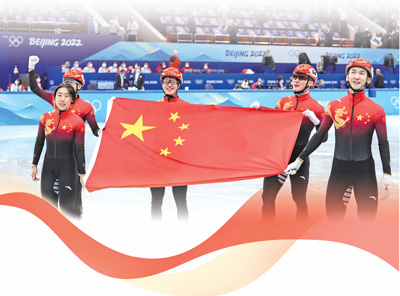为什么去那个地方?我喜欢的回答是,因为没去过。
 【资料图】
【资料图】
陌生是一种吸引和诱惑。东莞边上的樟木头我没有去过,得到召唤便欣然前往。
樟木头虽说是一个镇,可不是能小觑之地,这个镇与我们内地镇的概念有些不同。樟木头镇直属地级东莞市,相当于县区级别。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生活活跃,制造业发达,它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内地青年趋之若鹜的淘金之地、梦想之地。
有个场景我至今记得。那时我也不小了,读初中,年关将至,外出的人陆续回到村子里。一天傍晚我们几个伢在禾场上玩,村子东头走来两个穿着时髦的大小伙儿,颇有些意气风发,走近看是同族大哥。大冬天,他们只穿着单外套,尖皮鞋铮亮。我问他们从哪里回来,一个堂哥说东莞。说完很神秘地把我的手捉过去,往他腰上触摸,我摸到一圈硬纸似的东西。我问是什么?大哥神秘兮兮地将手指放到嘴边嘘了一声。我边上的军子说是钱。那么多钱。那一刻我羡慕不已,心想长大了我也要去东莞。几个堂哥是村子里最早一批去东莞——不知是否在樟木头镇——进厂的打工仔,回来乘一夜长途客车,把钱缝在内衣里扎在腰间,防被偷走。
长大后我也没去东莞没去樟木头,待我来时已届天命之年,我的堂哥们也早已离开了东莞。此次来不似我的堂哥们当年为生活梦想而来,我为“文”而来,来参加一个作家看樟木头的采风活动,更多缘由,还是想看看堂哥们当年的逐梦之地。
站在观音山麓半山酒店的窗前,樟木头尽收眼底。青山起伏之下,形成一方小平原,平原上“长”出高高低低的楼房,如蘑菇一般,被艳阳照得白亮,与青翠的山峦形成绿白对比的景致。一条叫石马的河流穿城而过,城分两岸,有了灵动之感。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小城樟木头蔓延着南国的苍翠风情和现代气息。
老实说,即使我刚踏上樟木头的土地,我也能肯定地说,这地儿对我的胃口。因为它保留着一种沧桑的旧感。街道不宽,甚至有些不规整的凌乱,街道两旁多是火柴盒式的私宅,三五层五六层不等,一楼标识着电子厂、眼镜厂,一溜过去,每家都是生产厂。拐个街道,倚在山边,突然就冒出十几栋三十多层的高层建筑群,森林一般立着。这些建筑外墙贴着浅色马赛克瓷砖,每家的墙上都留有窗式空调的空位,从这两点可以看出,这些建筑建于20世纪90年代。在那个年代这是高级时髦的装饰,而同时期我们内地镇上多为砖瓦房。穿行于樟木头的街巷,那个时代的活力和繁华会浮现出来。另一方面,在城市边缘地带,一些现代化的工厂拔地而起,如文玩厂、牙具厂等,它们又是簇新而现代的。与许多大动干戈改造的焕然一新的小城相比,樟木头保留了更多过去的印记,那是一代内地青年挥洒汗水和青春的地方,一个火热时代的背影。走过一些旧工厂门前,我眼前似乎飘过我堂哥们的样子: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刚从流水线上下来,有些疲惫,但眼里有年轻的光亮。某种程度上说,樟木头的“旧”里边保留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业化时代让一个南方小镇蜕变为经济大镇的印记,而这一点是令人怀想的。
看地图,樟木头位置很有意思,在东莞、惠州、深圳三座城市间寻找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便是樟木头,樟木头距离这三座城市都在35公里左右。地理上的便利让樟木头成为这些城市之间的“桥”和“后花园”,到香港罗湖口岸半小时车程,樟木头也因此一度有“小香港”之誉。
突然想起,我妻子年轻时在深圳待过十多年,便打电话问她有没有来过樟木头。令我颇为诧异的是,她说她从未到过樟木头。她说当年进深圳要通关证,如果谁没有通关证或者证件有啥问题,就会被送到樟木头去。她们那群姑娘都很怕去到樟木头,她至今也没有去过。
为什么去那个地方?我喜欢的回答是,因为那里有朋友。
对陌生之地的向往,构成了旅行的最大动力之一。这里边包含了人渴望冒险的本质,也包含了人渴望挣脱熟悉与庸常的好奇心。去一个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陌生的街巷、陌生的人群、陌生的习俗、陌生的气息——想一想都带劲儿;如果这陌生之中又有熟悉的光点,比如此地有一两位你的熟人或是朋友,即使朋友未曾谋面,那么,这陌生之中便有一种亲近感和期待感包围着你,那就更带劲儿了。孔子的话可以改一改:有朋在远方,不亦乐乎。
樟木头有我一个朋友,阿芬。我们未曾见面,但有神交之感。她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文学编辑,加上我们又是湖北天门老乡,年少时同饮一江水、同说一种话,自然亲切。阿芬早年到樟木头工作,后从事写作,写小说写散文,樟木头有个写作圈子,可能从圈子里知道有个老乡在文学杂志做编辑,稿子和信便寄来了,联系上了。早几年,我常在文学刊物上读到阿芬的文字,细腻、有情,有生活和人生的质感。但近几年她写得少了,不知为什么。我们淡淡交往十几年,一直未曾见面。
一想到陌生的樟木头有一个阿芬,我的樟木头之行便有了几分期待。一到樟木头,我便在活动手册上寻找阿芬的名字,赫然在列。第一天会程紧张,我没有见到阿芬,第二天到文联参观,展板上的作家介绍栏里我看到了阿芬的简介和照片,照片是一张头部侧面像,我按此在人群中搜寻,没有找到。待到去客家古建筑群三家巷参观时,一位中等身材、相貌端庄的女子朝我走来并同我打招呼时,我一眼就确认是阿芬,我们几乎同时说出对方的名字,两只手握在一起。文友加老乡异地相见,没有两眼泪汪汪,唯有亲切、开心和激动。我们聊了很多。她现在多数时间住在东莞,时不时也会回到樟木头来。我问她近几年怎么写得少了,她说有了二孩,生活占去了写作时间,女儿今年已经上小学了,可以回到书桌前了。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消息。
没来樟木头之前,早就听说樟木头有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集群,他们在樟木头购房居住,不时在此生活、创作和交流,名之“中国作家第一村”。这次来了才知道,阿芬是第一位在樟木头购房的作家,她在《翠景街89号》一文中讲述了她在樟木头的购房故事,63平方米的房子让她有了身体之家和心灵之家的感觉,她写道“没有自己的房子,连睡眠也是别人的”,一所异乡的房子终结了她的漂泊感,让她感觉安宁。可以说,阿芬见证了作家聚集樟木头的全过程。如今,“中国作家第一村”已经成为樟木头抑或东莞的文学品牌,它的意义正在外延为更宽阔的文学交流方式和文学地域标识的新形式。
我和阿芬商定,今年年关时在湖北天门老家相聚。
返程的动车上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阿芬给我投过一些稿件,我有刊发过她的作品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我竟然一时确定不了。
樟木头之行,还有一个见识上的收获,第一次看到了舞麒麟。舞龙、舞狮常见,舞麒麟我是第一次见识。三家巷的广场上,三只颜色各异、身形健硕的麒麟,在锣鼓和唢呐的热闹节奏声中,上蹿下跳,前突后撤,表演梳理、舔尾、采青、吃青等惟妙惟肖、干净利落的各种动作,热闹、喜庆、吉祥的气氛被渲染出来。舞麒麟兼具舞龙的气势和舞狮的敏捷。樟木头是东莞市唯一的纯客家镇,舞麒麟是明末清初由客家人从北方带来的,距今有四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樟木头的客家人有“龙生九子,麒麟为长”的观念,麒麟是他们的图腾。
为什么去那个地方?我喜欢的回答是,可能此生只去一次吧。